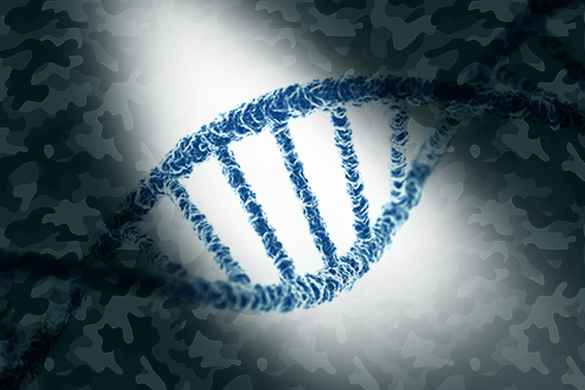新娘房內,新娘脫下晚禮服,肚子咕咕叫起來。
「乾掉這杯,新郎哥。」「今天大好日子,快喝快喝。」新娘聽到新郎的嬉笑聱,默默地換上裙褂。
為了這套裙褂,她和新郎吵了無數次,她代表的是她自己,他代表的自然是他的母親,也就她當時的未來奶奶。最後,婚期越來越近,新娘不得不屈服,選了一套出租少於五次的貴價裙褂。裙褂店就在婚宴場所的附近。新郎說,好啊,這樣夠方便。
大約一年前,新娘提出找個地方辦個酒會,宴請親戚好友出席。她連地方也物色了,是一間露天酒吧。新郎覺得人生大事,必須隆重,但沒有說辦酒會如何不隆重。她知道未來奶奶想大排筵席。然而,兩人的聯名戶口加上個人戶口的儲蓄總額,連支付酒店的最低要求也不足,唯有選了這家位於太子的酒樓。於差不多九個月的籌備中,這是唯一新郎讓步的一次。當然,真正讓步的是他母親。
「太子好啊,交通方便,親朋戚友都一定會來。」新郎這樣說服自己的母親。兩人一起的時候,會特地到元朗買老婆餅,在大埔拋許願樹擲寶牒,去港島不坐沉悶的地鐵,而是迎著海風坐天星小輪。想不到新郎在這件人生大事上,事事以方便為先。後來,新娘洞悉到事事方便是由未來奶奶出主意。地方是奶奶選的,酒席是奶奶選的,甚至身上裙褂的繡線都是奶奶選的。「這樣不好嗎?有人出面擔當了這件麻煩事,我們就可以專注在往後的日子。」當然,新郎沒有說明何謂往後的日子。
對鏡一照,新娘還是第一次看見自己穿上全套裙褂的模樣。化妝桌上的手機震動幾下,新娘在版面上看到一個未閱短訊,寄件人是楊樹偉。她看看正在忙著拿金器過來的姐妹,迅速地打開了短訊。
「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,恭喜你。」
新娘臉上一熱,心好像在口裡跳動。伴娘和姐妹們把一件又一件的金器懸在她那雙幼小的手臂上。她早就忘了那件金器是哪位親戚送的。
走出新娘房,外邊有一半以上的賓客都是她不認識的夫家親戚。每個人都對她投以熱切的目光。新郎的臉蛋比手上的酒還要紅。奶奶不忘向大家展示新娘臂上的金飾,新娘這才了解一場婚宴的主角,從來不是兩位新人,而是金器。金器夠不夠多,夠不夠重,就是這場測試的基準。新娘雙臂勉強舉起倒了假裝是酒的普洱,似乎在這件事她的婚宴是合格的。
一張張笑得很高興的紅臉,浮現在自己眼前。新娘彷彿聽到攝影師唸佛般說著「新娘,笑得開心點。」新娘整天都在笑,臉頰僵硬,卻沒有半點笑聲在嘴裡逃出來。四面八方的賓客都以兩倍的速度移動,新娘的手沒有伸出去,杯子已叮叮叮叮響個不停。新娘聽到三十二年農曆新年加起來還要多的恭賀說話,才意識到祝願人婚後產子有如此多的說法。
回到新娘房,她褪下金鐲。幸好毋須換衣服。臀部還未適應椅子的承托,奶奶衝進來喊道:「三叔公要走了,我們要出去送客。」於是新娘又離開了位子,快步到了酒樓的入口。
新郎由兩個兄弟左右門神般扶著,雙腳不住在地上滑動,好像穿了滾輪。新娘看見已成為丈夫的男人有張紅紅的娃娃臉,總算開了眼界。第一個上來的是三叔公,然後是兩三個單獨的賓客,接著是四人家庭。一個小女孩爭著要和她握手說恭喜。桌上的美點雙輝沒動過多少,靜靜地被遺留在由冷清取代的宴會廳。
新郎忽然咳嗽起來,然後整晚喝過的酒、吃過的菜,水泉般噴射出來。賓客跳了開去,本來扶著新郎的兄弟忙去取熱毛巾。奶奶一邊不住地跟賓客道歉,說新郎太高興,一邊用毛巾抹著那一塌糊塗的禮服。
一隻大手握著新娘的右手。這種體溫,這股力道,熟悉而遙遠。這隻大手,竟然把新娘在眾人的眼底下拉走。新娘那雙紅鞋,跟著那人快速的步伐往下跑。他們經過那租借裙褂的商場,跑過馬路。太子地鐵站出口放滿了祭祀品,新娘一身紅衣走過,竟然沒有惹人注目。路過旺角警署外的水馬,他們來到一家米線店。
「要吃嗎?」楊樹偉沒有等新娘回應就打包了兩碗米線。
他們在附近公園的長椅坐下,打開蓋子,花椒味撲鼻。
「吃完了就換衣服,我們一起走。」楊樹偉從背包取出一個塑料袋,裡面是衛衣和牛仔褲。
「去哪裡?」米線一下肚,新娘本來浮浮的雙腳也踏實起來。
「我們一起的地方。」
新娘的木筷攪著赤紅色的湯。「你遲了。」
「就因為你簽了那張結婚證明書。」
新娘放下碗子,站起,拍拍裙褂。幸好沒有沾上半點湯水。
「你有一年的機會,偏偏今天才出現。」新娘信步離開公園,賸下楊樹偉在公園。
新娘沒有回去酒樓,也沒有回去跟丈夫合租的房子,她登上一輛泊在附近的紅色小巴,臉龐貼著金屬扶手,慢慢地閉上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