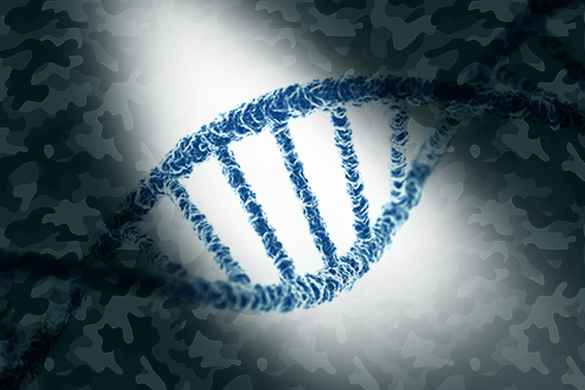車窗外照進來的陽光,令良行幾乎睜不開眼。他身處平治房車的後座,聽到秀惠正在指揮女兒巧雲從車尾廂取出背包。
「叩叩。」秀惠敲敲車窗。巧雲叫道:「爸爸,你再不起來,我們就先走啦。」良行伸個懶腰,背脊發出爆米花的聲音,吁了口氣。車內空調的冷氣逐漸消散,良行急忙步出車外。看看四周,良行問:「我們在哪裡啦?」
巧雲沒口氣的說:「那邊是郊野公園的入口啦。」兩母女慢慢走離這輛用了差不多八年的平治。良行追上去,伸手去拿秀惠手裡的保温箱,卻被她避開。
除停車場走上去一段路比較平坦,都是向上的斜路。儘管身負重物,秀惠和巧雲這裡一蹤,那裡一踏,竟然走得比良行要快得多。良行看著她們倆越來越遠的背影,倒沒有追的意思。
山路越走就越陡峭,平整的梯級只是偶然一見,更多是石塊和高及腳踝的雜草。秀惠和巧雲行山杖撐著地,依然健步如飛,巧雲還有閒情用手機拍照。良行哈著腰一步一步走,就像在尋找丟在地上的眼鏡似的。
「爸,你在哪裡?快點啊。」巧雲的聲音在上面響起。
「你再不走快點,我跟媽就把你留在這裡啦。」
良行可以想像秀惠交叉雙手,一邊眉毛上挑的模樣。他咬牙用力向上,一口氣快走幾十步,轉角看見兩母女坐在樹蔭下休息,早就氣喘連連。
良行看到巧雲正從印上卡通人物的瓶子喝水,才想起自己沒有帶飲料。離家前明明在冰箱拿出一罐可樂,可是放在秀惠手裡的保温箱。
「哎,給我喝一口。」
「不行。」
「為什麼不行?」
「瓶子是我的,水是我的。」
「這個人物是白雪公主嗎?」
「不,是艾莉沙。」
「沒聽說過。」
「魔雪奇緣都不知道,孤陋寡聞。」
「連孤陋寡聞這個詞也知道,我女兒真厲害。」
「是老師教的。」
「哎,你不是口渴嗎?」秀惠遞上一個保溫瓶。良行扭開蓋子,正要仰頭喝裡面的東西,「喂,我不想喝你的口水尾。」良行忙把飲料倒在倒轉的蓋子,原來是冰紅茶。
「我們快到頂沒有?」
「還未,才走一個小時。」
「這段路你走了多少次?」
「總有七八次吧。」
「怪不得你走得這麼快。」
「巧雲也是第一次走,倒跟得上我的步伐。」
之後的山路沒有大樹遮蔭,毒熱的陽光照下來,良行的額頭聚著豆大的汗水,腋下背脊的運動裝都濕出來。
為何好像怎麼走也走不完?為何我要跟著來呢?如果跟客人打高球不是比這強嗎?
秀惠和巧雲變成前路的兩個小點。
良行覺得雙腿越來越重,每踏一步,腳板傳來又酸又麻的痛楚。手機在口袋裡震了幾下。原來是秀惠發來的即時短訊。
「我們已經到頂啦。」
然後是一個語音訊息,播出來卻是巧雲的聲音:「爸,我們不等你啦,先把午餐吃光,哈哈。」
到達山頂之後,良行第一時間脫下運動鞋,按摩那腫腫脹脹的腳弓。巧雲從背包取出自拍棒,與秀惠拍照。她們倆踏著一塊大石頭,身後就是個懸崖。
秀惠和巧雲一起掉下去的畫面在良行的腦海浮現。她們的嘻笑變成慘叫,良行聽來卻無比暢快。
良行坐在巧雲鋪在樹下的墊子,捏著小腿。
兩母女回來,巧雲從背包中取出午餐,是上午弄好的三文治,餡料有些是火腿芝士,有些是蕃茄雞蛋。良行咬一口,吐出麥子。秀惠鼻孔裡哼了一聲,良行將目光放到其他地方,不和秀惠的雙眼相觸。
良行狠灌一口紅茶,才勉強把麵包嚥下去。如果和客人打高球,午餐一定是牛柳佐以法國紅酒。
巧雲和秀惠都是小口小口的吃,沉默不語。良行才意識到她們兩母女是如此的相似。
午飯後的路都是往下的,左轉右拐,三人進入樹林。本來的石路,也慢慢由滿佈濕葉的泥路取代。良行要蹲下來,左腿伸前踫到實地才敢把身子俯下去。
兩母女行山杖的篤篤聲越來越遠。
「喂!你們在哪裡啦?」
「你跟著樹枝上的帶子就行啦。」果然每幾步就有繫上紅色絲帶的樹枝,應該以前一些山客留下來,為其他人指引。
有了這個提示,良行越走越快,不久就聽到秀惠和巧雲的聲音。
「爸還沒有到呢?會不會在山裡迷路呢?」
「迷路倒不會吧。他太少運動啦,只會在周末打高球。」
「高球也算是運動嗎?揮揮桿子,十八個洞之間都有車代步的。」
「看他肚子就明白,我叫他去身體檢查他不肯,還惱怒我嘲笑他。」
「今天為什麼叫他來?還要選這路線。」
「就是讓他知道這個真相。」兩母女的聲音就在下面不遠的地方。
良行多希望秀惠可以看到他打高球的風姿,讓她知道體力該用在什麼地方,而不是在樹林裡玩家家酒。
這時秀惠又傳來一通語音短訊,也是巧雲的聲音:「爸,你在哪,我跟媽等了很欠,再不來就把你留在這兒啦。」
良行彎腰拾起一塊拳頭大小的石頭,向著聲源擲出。他沒有扔中巧雲的意思,這一擲也是隨手而出,只是想嚇嚇她,讓她知道老爸的厲害。
石頭直飛向下,接著傳出擦過樹枝樹葉的聲音。
秀惠的尖叫響徹整個樹林。
良行的電話震起來。是秀惠。良行顫著手按綠色的接聽鍵。
「良行,快來,巧雲受傷了。」
「你們在哪?」
「離你不遠啦,唉,我不應該走這條路的……」
良行一掛線就跑下去,豈知地上太滑溜,一屁股就坐在濕葉上,一股涼意直透進去。他也不理會褲子有沒有留下泥濘什麼的,站起來繼續走,不久又仆倒。這次在山路上滾下去,額頭撞中一塊硬石,痛楚很快散佈到整個頭部。良行手背一抹,腫了一大塊。
「喂,你沒事吧,不要先弄傷自己啊。我可不想多照顧一個人。」
良行按著額頭,踉蹌踉蹌走到秀惠面前。巧雲躺在身邊,雙目緊閉,一副熟睡的模樣。
「我已為她包紮傷口,只是她沒有醒過來。」
「她怎麼啦?」
「我們在等你啦,忽然不知哪裡掉下一塊石頭,擊中她的頭。」秀惠說。
良行蹲下來,只見巧雲的頭顱包了毛巾,毛巾上有乾涸的血跡,遮蓋不了紫黑的瘀傷。她臉旁有塊拳頭大小的石頭,良行忙把它放進褲袋。
「那該怎麼辦?」
「我叫了救傷車,不過他們說上山救人有些困難。如果傷勢不大嚴重,就希望我們可以帶她到會合點。」
「這樣也不嚴重?」良行一陣亂踢,一塊泥巴直飛到路邊一塊石牆。良行這才留意到,從這裡連綿下去,是一幅無間斷的石牆。上面是些黑色藤蔓,重重疊疊不定神是沒法分辨的。
良行看看地上的巧雲,又看看滿臉關切的秀惠。「來,把她放在我背上。」
「你真的行嗎?」秀惠一臉狐疑。
「快啦。」
秀惠依言照做。良行大喝一聲站起來,雙腿震抖,總算沒有摔倒。
「你帶路,我們走下去。」巧雲那約五十公斤的身體完完全全的壓在良行身上,良行每走一步,肺裡的空氣就像被強行抽出。良行看著秀惠的背包,腳下的濕泥爬到鞋邊。
良行感到腳掌火辣,秀惠的背包在樹影之中只賸下那熒光的標誌。「停下來停下來,我走不下去啦。」只見秀惠回過頭來,一臉不解。
「我們走了多久啦?」
秀惠查看手機後說:「現在是五點三刻啦!應該快到啦。」
「這條路線你之前走過?」良行想起剛才兩母女在樹林裡的對話。
「走過呀。」
「那通常需要多長時間?」
「我走的話,不會多於四個半小時吧。」
「那也太奇怪,就算我走多慢,加上揹著秀惠,也沒可能多出那麼多時間出來。」
秀惠拿出手機又點又張,說:「我們還在路上,地圖程式說我們離會合點還有約二十分鐘的腳程。」良行忍著腳掌的痛楚繼續走。
那二十分鐘的腳程,好像比二十分鐘要漫長。樹林中只有太陽的餘暉。路邊的石牌越來越密,幾乎是貼著的。
秀惠的電話響起,她接聽。良行趁機蹲在地上休息,鼻子都是腐草爛葉的氣味,聽到秀惠說句「我們快到了」和「地圖程式說我們只有十分鐘左右」之後就掛線。
「是救護員。他們說在會合點已經等了半個小時,我們五分鐘內不到他們就會離開。」
「現在地圖程式怎麼說?」
「還有十八分鐘。」
「沒可能,一定是手機程式出錯,我們最少走了十分鐘。」
秀惠忽地打開手機的電筒,逕自走下去。「喂,你打算去哪?」
「要不你跟巧雲在這裡待著,我跟救護員會合,再領他們上來。」良行也來不及反對,秀惠就一股腦兒跑下去。
秀惠的背影逐漸和樹林的影子融合一起,連背包發光的牌子也看不見,良行嘆口氣,蹲下來將秀惠放在一旁。巧雲的身子一觸地,立即卷伏成嬰孩在母體的姿態。良行伸展一下身體,察覺到左邊有些動靜,信眼看去,牆上的藤蔓似乎在蠕動,近看有點像一個又一個張嘴欲叫的臉。他後悔剛才沒有問清楚秀惠,上次走這段路的時候,有沒有這些藤蔓。
良行取出手機一看,主頁面沒有任何通知。他解鎖後立即發短訊給秀惠,問她跟救護員會合沒有。按下發出鍵,訊息右下角出現小時鐘的圖樣,也就是沒有發出去。良行連試幾次,畫面就出現三個小時鐘,連半個剔號也沒有。
他全身打個疙瘩,腦海中冒出一個念頭:秀惠跟自己用同一個電訊供應商,那她又如何接到救護員的電話。他絕不相信巧雲會在這樣的事上跟自己開玩笑,可是……
良行一步併兩步回到巧雲那處,她依然在伏在地上,姿勢跟剛才沒有半點區別。他把女兒揹著,拿起隔熱箱,正要邁步向秀惠消失的方向走。
然後,良行回頭往上走。他依希記得接到秀惠電話時,眼角看到有條坌路。良行冒黑往上爬,摸到樹枝就抓緊借力,突然腳踝一緊,整個人就仆倒。整個腳踝不知什麼時候纏上蔓藤。他花很大力氣就把它們拔掉。當良行回到他擲出石頭的地方時,汗水已滲透運動服。
應該是向這裡走吧。良行眼前黑壓壓一片,天上烏雲完全遮住月亮,半點光也沒有透出來。他小心翼翼地從懷中取出手機,巧雲像個熟睡的孩子伏在他背上。他打開手機的電筒,面前立即出現一條山路。
良行一步算一步的走,跨過攔在前邊的樹枝。地面比剛才還有潮濕,良行不敢踏在石頭,怕一滑就跟巧雲一起在山坡滾下去。他的眼鏡全是霧氣,抹不了就只好咪著眼睛、雙手伸前的走。
當酸痛由腳掌傳到小腿時,背上的巧雲呼口氣,「哎」一聲。
良行說:「哎,你好嗎?」他聽到自己有些哭音,眼前也開始模糊起來。
「爸,這裡是什麼地方,我為何在你的背上?」巧雲從良行的背上跳下來。
「你媽說,你給一塊石頭打中腦袋,暈了過去。你媽下山跟救護員會合,我們我們……」
「爸,我想喝水。」巧雲挨在山路一旁的石牆上。
良行把那印上艾莉沙的水瓶,遞給巧雲,自己就打開隔熱箱,拿出久違的罐裝汽水。
良行咕嚕咕嚕的喝了半罐,巧雲說:「汽水多糖,多喝會胖。」
「你別管我。」
「你不小了,真的要喝一整罐?」
「好啦,你要喝一口嗎?」說著向巧雲遞出汽水。巧雲接過汽水,喝一大口,發出滿足的嘆息。兩人對望一眼,哈哈大笑起來。
一陣濕葉子被急步整爛的聲音傳來,巧雲站起來說:「是媽!媽!」
良行正想回頭,耳裡聽到「啪」的一聲,頸後被抽打一下,痛得他半跪下來。他聽到秀惠的聲音說:「叫你們不要走開就偏不聽,害我找了那麼久。」
良行剛回頭,眼角又中一下,一陣紅光撲入眼簾。他捂著傷處,模糊中只見秀惠舉起半截兒臂粗的樹幹,急忙後退。腳踝絆到樹枝,立即向後仆倒。秀惠揮下樹幹。良行前臂擋了幾下已經發麻,舉不起來,左頰一陣劇痛,然後聽到鼻腔裡「卜」的一聲,帶著一陣血雨仰天倒下。他剛轉過身想爬走,背脊又吃了幾下重的,支撐著身體的雙手軟下來。良行的臉半浸在濕泥,一陣冰涼。
「不要打啦,不要打啦。」良行全身上下無處不熱辣辣抽著痛。
「巧雲,你走開。」
「我不走。」
「你答應了我什麼?」
「我……」良行翻了身,半坐在涼涼的地上。
「滾開!」秀惠的聲音在良行的耳鼓裡迴盪。他本來已昏昏沉沉,這時卻半醒過來,感到褲袋裡有些東西磨著大腿怪不舒服的。良行伸手進去,摸到塊濕濕的硬物。
「你,你說到了山裡,我們就會好像以前一樣。」巧雲說。
「那你就不要阻手阻腳。」說著秀惠拉開巧雲,一腳踢倒良行,跪在他胸口,把樹幹的尖端對準他喉頭。良行這時看清楚,秀惠臉上正流著混了塵土的汗水,就像鹽地一道道灰色的河。
秀惠舉起左手,用力把樹幹刺下去。
「噗。」石塊擊中頭顱沉沉的聲音在寧靜的樹林份外響亮。
秀惠只不過跌出了幾步。她右眼充血,臉頰擦傷一片。塗了口紅的嘴巴笑了,牙齒反映著黯然的光。
良行想站起來,可是雙腿完全使不了勁,屁股離地數公分後就頹然坐倒。秀惠的運動鞋就在面前。有幾滴血掉落在鞋面上。良行不敢抬頭。
一個瘦小的身體攔腰撞在秀惠身上,她腳步交叉,就往旁邊的山坡掉下去,半點叫聲都沒有。
良行氣喘喘的站起身子,看看手裡染血的石頭,然後把它拋在一旁。
「你媽剛剛瘋了,我們是為了保命才這樣做。」巧雲點點頭,臉龐蒼白。
良行拍走身上的泥土,只把雙手弄髒,衣服上的污跡有增無減。
「巧雲,你可以走路嗎?」她再次點點頭。
兩個人走下去,巧雲驚叫一聲,指著前面。樹下石上伏著秀惠那軟塌曲折的身體。地上的濕葉伸出一條條的藤蔓,圍繞秀惠,轉眼間把她完全淹沒。黑影逐漸地擴張擴大,就像是個有人吹氣的汽球,然後爆散開去。
巧雲雙目張大,卻看不見一條藤蔓已纏上小腿。藤蔓急縮,扯跌巧雲,在地上拖行,把她拉向石牆。
良行奮力前撲,剛好抓住巧雲的手腕,左手隨即抓住手肘。良行看見藤蔓已爬至巧雲的腰肢,然後是後背,然後是頸項,然後是下巴。她雙目蒙上一層死灰,瞳仁倒映著襲向良行的藤蔓。
良行雙腿動不了半點,力氣給一絲又一絲的抽掉。他感到喉頭被縛上一條鍊子,用力收緊,把最後一口氣擠出去。
良行氣絕後,黑色的藤蔓捲著三人身體,拉進石牆。牆身慢慢浮現出紋理,遠看像三張正在微笑的臉。